美國《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是一份涵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領域,包括國家安全各事項的綱領性文件,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頂層設計,為研究和把握未來美國安全政策走向提供了重要依據,具有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2022年10月12日,美國白宮于當地時間發布了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第一部正式報告。報告提出,未來十年對美國和世界而言是“決定性的十年”(decisive decade),并就此提出了涵蓋各領域全方位的全球戰略,闡明了美國如何看待世界安全形勢、尋求什麼樣的未來以及怎樣實現其戰略目标等重大問題。

圖1 美國《2022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封面
(圖片來源:美國白宮網站)
這一版本與2017年特朗普版《國家安全戰略》相比有明顯變化,進一步強調了對華全面競争和戰略包圍,體現出對中國發展潛力及抗壓能力的深度焦慮。文中有大量涉華内容,正文全篇共提及“中國”50次,将中國單列了一個模塊于美國“全球優先處理事項”中。其中,對中國的地位、實力等各方面做出全方位的評估并突出強調了下一個十年一系列對華政策,反映出拜登政府對華的鮮明态度,對接下來中國外交政策與對外關系走向将産生重大影響。從語義分析的情感傾向切入,這份文件對“中國”的語義表述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帶有遏制和競争傾向的“負面表述”;二是僅陳述客觀事實的“中性表述”;三是認可并支持中國做法的“正面表述”。通過詞頻數目統計和情感屬性梳理,可以得到如下語義分析扇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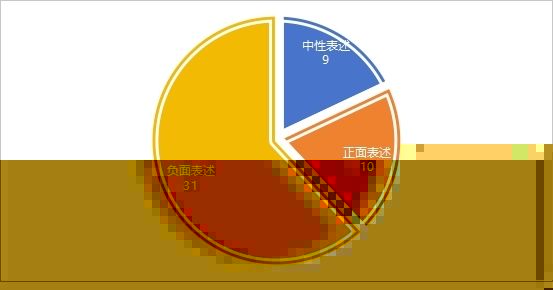
圖2 美國《2022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涉華詞頻語義分析
從國際人才工作的視角來看,近年來中美科技人才交流工作面臨的困境都是美國對華整體戰略的具體體現,兩者之間是全局與局部的關系。為進一步理清當前美國在對華高科技領域打壓策略的宏觀脈絡,準确研判未來中國對美高科技引才引智工作困難的廣度與烈度,有必要立于國家科技戰略與人才戰略的視角解讀這份報告。
一、當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總體思路解讀與研判
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大前提是“美國優先”,不論是上一階段的“對華接觸”,還是這一階段的“對華脫鈎”,都是基于美國利益至上理念的策略選擇。當“美國優先”理念被置于一種零和博弈的競争語境之中,犧牲他國利益是美國核心戰略目标實現的必然。
由于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主導思想相比前任政府已經出現重大轉變,所以這份報告在繼承前任政府國家安全利益護持路徑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出現若幹不同程度的戰略路徑轉型。通過與前任特朗普政府以及“臨時指南”的詳細比較,這份報告存在的最大亮點便是重新界定了中國的角色和未來的中美關系。
報告指出中國給美國帶來“影響最為深遠的(most consequential)”地緣政治挑戰,并三次提及中國是一個既懷有重塑國際秩序意圖,且重塑國際秩序的相關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也越來越強的競争者。
首先,報告專門對中國和俄羅斯給美國帶來的安全威脅差異進行了識别,并首次對中俄兩國挑戰的優先級做了明确排序。對于美國而言,俄羅斯雖然是幹擾全球穩定的一項因素,但所帶來的持續且緊迫的地區安全秩序影響僅僅局限在歐洲,并沒有中國那種全方位、多譜系的影響能力。反觀中國,雖然其在印太地區影響最為強烈,但具有重大全球影響力。在中俄兩國聯系日益緊密的背景之下,美國保持針對中國的長久競争優勢,要比限制俄羅斯的危險性小得多。未來十年是美國取勝(out-compete)中國的“決定性十年”。可以說,這份報告已将中國的挑戰地位擡升至冷戰結束以來的曆史最高水平,不但給未來的中美關系确立了明确的“競争”基調,也必然會使中國未來的國際處境變得更加艱難。
其次,雖然報告所指出的美國對華具體戰略路徑,沿襲了此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提出的“投資、結盟和競争”三大要素,但較此前的表述也有一些新思路、新内容。例如報告聲稱中國對美國存在全方位、多譜系性的競争,因而美國對中國的威脅遏制也具有整合性,具體體現在五個方面:軍事與非軍事的領域整合、關鍵地區與美國本土的整合、沖突範疇的整合、美國各政府部門間的整合、盟友與夥伴間的整合。在外交政策與國内政策分野已然打破之下,美國一方面加大對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進行“戰略性公共投資”,以國家力量助力提升私營部門實力,另一方面在印太地區以“小多邊主義”形式打造孤立中國的盟友與夥伴體系,将給中國帶來前所未有的艱難外部處境。而在安全領域,在印太與歐洲地區日益聯動的背景下,北約也不同程度地針對中國出現所謂的“全球化”轉向,尤其是在網絡空間安全和氣候變化等議題上。鑒于此,未來中美關系的議題聯動将不可避免走低,中國的經濟與安全也将因此形成惡化之勢。
再次,在“民主—獨裁”對立的主導思想下,中美之間即使在應對跨國性“共同挑戰”上存在共同利益,合作空間也将被嚴重壓縮。報告承認中國對于全球“共同挑戰”存在重要影響,特别在氣候變化和全球公共衛生問題上尤為突出。然而,報告始終強調中美在政府和制度層面所存在的深刻分歧,在應對“共同挑戰”時不僅不支持議題聯結(linkage of issues),還抨擊中國将“不相關的議題設置為合作的前提條件”。而實際上的真實情形恰好與此相反。因為所謂的跨國性“共同挑戰”往往同意識形态分歧無關,将意識形态上的“民主—獨裁”對立作為應對“共同挑戰”的前提本來就是将不同議題強行捆綁,所以也必然會壓制合作空間、扼殺合作機遇。美方如繼續堅持這一點,就是在應對跨國性“共同挑戰”上創設不必要的人為障礙。
誠如報告所言,當今世界正處于曆史“拐點”,這與我們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論斷相一緻。通過對今年報告的解讀,可以認為,自奧巴馬2009年訪華以來所确立的以戰略互信、經濟合作為基礎的中美關系已不複存在,中美已進入由美方單方面定義的全面競争、戰略遏制的全球性對抗态勢。這種态勢的發展不僅可能表現為非暴力的政治與經濟貿易對抗,甚至可能在局部升級為武裝沖突。推動中美經濟與科技全面脫鈎,則是實現其戰略意圖的重要手段。有鑒于此,對中美國際人才與科技交流大環境不可存有僥幸心态,要充分認識鬥争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所要求的,“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二、美國推進對華遏制戰略的核心策略及其影響
(一)壓制對華高科技産業供應鍊
以國家安全為借口,以“長臂管轄”為支撐,以供應鍊壓制為策略,以戰略資源争奪為目标的對華遏制戰略,這已成為美國制定國内外政策的指導思想。報告中明确寫道,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标之一是在競争中壓倒中國,“保持對中國長期的競争優勢是我們的第一要務。”近期,美國明顯加大了對中國國際化人才培養與引進工作的打壓力度,從過去的有所顧忌、定點打擊演變成現在的不惜代價、全面打擊,甚至不考慮這些措施在短期内對美國本土高科技産業的負面影響。我方要将這種看似孤立、非理性的政策選擇置于美國整體性國家戰略體系中加以考察,絕不可以低估其政策推進的戰略決心與執行能力。例如,美國司法部宣告終止“中國行動計劃”,絕不代表放棄了其阻斷中國國際化引才引智工作的企圖,而是一種将臨時性、局部性措施替換為常态化、體系性打壓的策略調整。此前美國商務部強令各大高科技公司提供其敏感供應鍊信息,表面上是為了“解決芯片供應困難”,其真實目的是搜集我國高科技産業鍊與美相關企業技術與人才依存關系的重要情報信息,作為其後續全面精準打擊的決策依據,用心險惡,布局深遠。近期美國在涉華高科技企業推行的全面服務禁令僅是常态化打壓的開始,我方需要為即将到來的更加嚴峻的封鎖形勢和更加嚴密的封鎖措施做好充分準備。
(二)強化政府對人才交流的幹預
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大力倡導所謂“自由市場全球化”。在人才領域,放手由企業、高校與科研機構主導與中國的人才交流,積極吸引中國留學生與科研人員,以獲取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科技人才。這一時期,高端人才呈現近乎單向流動态勢,高精尖技術在華轉移趨勢亦不明顯。在1993到2024年,中國每年派出留學生赴美人數從2萬人左右提升至近35萬,而學成歸國比例隻有1年高于40%,其餘年份均在30%上下徘徊,選擇歸國的已在美就業的高端人才比例更低。2010年以後,随着中國國家實力的高速提升,這種局面開始出現逆轉,高科技人才回流呈上升趨勢。2007年起,中國赴美留學生歸國比例持續上升,到2011年已超過50%,在美已就業人才回國數量也顯著增加,高科技領域向中國的技術轉移與擴散趨勢日漸明顯,這一趨勢被美國解讀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并認為僅依靠市場力量已不足以遏制這種威脅。報告所提及的“戰略性公共投資”可被視為美國工業發展戰略由市場導向向國家幹預轉向的階段性達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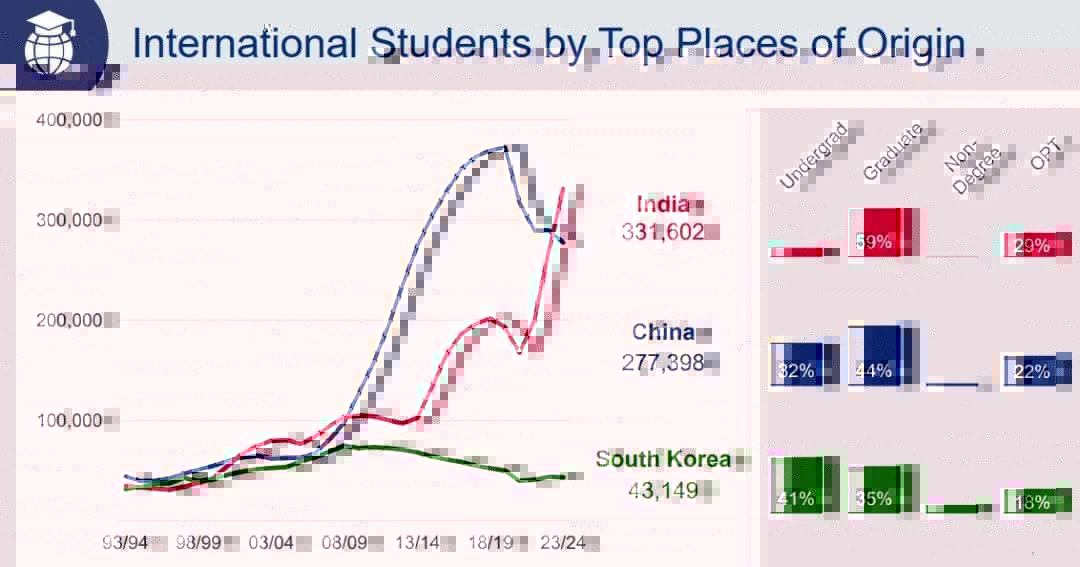
圖3 赴美留學生的主要來源地
(圖片來源:Open Doors網站)
伴随着美國政府以國家意志幹預本應由市場導向的商貿與人才交流,中國的高科技外向型發展将面臨更為露骨的制裁與打壓措施。美國政府會更加頻繁地利用簽證限制、經濟制裁,甚至刑事追訴等手段幹擾中美正常人才交流活動,進而限制涉華技術輸出與服務。美國在“中國行動計劃”終止之後的一系列舉措說明其政府幹預市場化自由人才流動的決心不僅沒有減弱,反而變本加厲,逐漸轉向常态化、制度化。
(三)構建對華科技封鎖聯盟
自特朗普政府掀起對華貿易戰以來,美國選擇了以一國之力壓制中國發展的策略。趨勢表明,在這種一對一的戰略博弈中,美國并不能占到便宜。依靠冷戰後全球化發展形成的多元化格局,中國可以通過與友好國家強化協作、轉移風險等措施繞過美國的封鎖打壓。美國對中國發動的單方面貿易戰反而在多個領域傷及自身,這種以一國之力赤膊上陣的競争策略已經難以為繼。此前,美國的“單打獨鬥”主要出于對自身實力的盲目自信與對協調多國反華戰略部署的缺乏耐心。現在,美國清醒地認識到中美實力對比和多邊國際格局不允許其一意孤行,就開始展現更大的戰略耐心,追求更現實的“拉幫結派”策略部署,報告更是頻繁出現“同盟”(coalition)字樣。美國通過玩弄所謂“民主價值觀”概念,實行地緣政治操弄,誇大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矛盾争端,試圖強行将各國拉上其對抗中國的戰車,比如無端指責“中國的強硬行為引起了其他國家的反擊,并出于其自身的合理原因而捍衛其主權”,并宣稱“我們對印太地區和歐洲地區的民主國盟友和夥伴之間在技術、貿易和安全方面的發展和聯系高度重視”。通過炮制“中國威脅論”,美國将中國在科技、貿易和區域影響力方面的發展扭曲為對周邊甚至歐美國家的安全威脅,以實現其建立對中國戰略包圍圈的目的。顯然,對比此前對華壓制策略,這種包圍戰略更加成熟,一旦成功,效果也更明顯。目前為止,其他國家僅是被動配合美國的措施,以合規為基礎協助阻止來自美國的技術與人才向中國的流動。而歐洲發達國家本身具有雄厚的科技實力與人才儲備,除少數美國“忠實盟友”會主動地限制其自主掌握的技術與人才向中國的流動之外,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依然願意與中國開展經貿技術合作,實現互利共赢,成為我們對外人才工作的突破口與緩沖帶。一旦美國實現其所謂最廣泛聯盟之構建,結盟的約束性義務将迫使這些國家主動限制和監管與中國的技術交流與人才流動,我國對外人才工作将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
撰稿人:澳门永利集团304官网手机國際人才法律服務研究院專家團隊
